后唐的发展史是什么 沙陀的族源是什么?
2022-09-06 10:55:04 来源:经济头条
后唐(923年-936年)是五代十国时期由沙陀族建立的封建王朝,定都洛京(今河南洛阳),传二世四帝,历时一十四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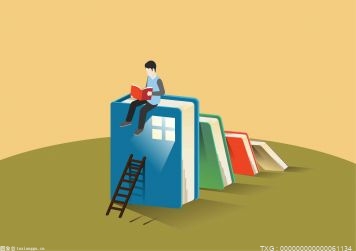
后唐是五代十国时期统治疆域最广的朝代。"五代领域,无盛于此者"。"时梁晋吴蜀四分天下,后唐以一灭二,天下四分已得三分"。
891年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被封晋王,建立前晋,从此割据河东。 907年朱全忠篡唐,建立后梁,晋国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,期间晋国视梁朝为闰朝,仍奉唐朝正朔。 909年李克用去世,子李存勖即晋王位。 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,改元同光,沿用"唐"国号,升魏州为东京兴唐府。 同年底李存勖灭后梁,定都洛京;926年灭前蜀王衍;928年南平高从诲内附;930年南楚马希声内附;936年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为代价,借辽兵攻入洛阳,称帝建立后晋,后唐灭亡。 937年,李昪在江南建立南唐,延续大唐正统,南唐也是十国当中版图最大的王朝。
后唐疆域广阔,主要控制着中国北方地区,东接海滨,西括陇右、川蜀,北带长城,南越江汉;925年至933年,南方诸国除南吴、南汉外皆奉后唐正朔;930年,后唐控制国土到达极盛;有今豫、鲁、晋、冀、湘、渝诸省,陕、川、鄂之大部,宁、甘、黔各一部分,以及苏、皖淮北等地。
五代十国,天下分崩,中原五朝更迭。历来皆以中原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为正统一脉相承。然五代末及宋初,皆视后梁为闰,究其原因,是因后唐以中兴唐祚为号召,用唐天佑年号,复唐立国,且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皆出自河东集团。
中和三年(883年)沙陀族将领李克用因收复京师长安有功被封河东节度使,治太原府。大顺二年(891年),受封晋王,建立晋国。 由于朱全忠曾有意暗杀李克用,但被李克用侥幸脱身,所以李克用与朱全忠誓不两立。 天佑四年(907年)朱全忠篡唐建立后梁,李克用仍用唐天佑年号,晋国成为后梁北方最大的威胁。 天佑五年(908年)李克用死后,子李存勖即晋王位。
天佑七年(910年)朱温企图彻底消灭义武军和成德军,派大军进赵地。成德节度使赵王王镕无法抵御后梁的进攻,向晋国求救。 同时义武节度使北平王王处直也遣使表示愿意归附晋国。李存勖把握时机,派大军救赵,与梁军大战于柏乡,大败梁军。柏乡之战后,义武军和成德军都归附于晋国,使得晋国的势力逐渐强大。
天佑八年(911年)卢龙节度使燕王刘守光称帝,改元应天,国号"燕",史称"桀燕"。 李存勖以平叛为名,大举进攻燕国。天佑十年(913年)晋国灭亡燕国,杀刘守光于太原。 经过此战,河北之地大都归属于晋,为晋南下灭后梁奠定了基础。
天佑十二年(915年)天雄节度使邺王杨师厚去世,梁末帝企图分魏博为两镇,魏博军乱,相继以州县归降晋国。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后,魏博诸州为晋国所有。自此,河朔三镇全部都归入晋国的统治之下,使得梁晋形势发生逆转,晋国由弱势一方变为强势一方。天佑十五年(918年)晋王李存勖率军攻梁,在今河南胡柳陂一带与梁军大战,晋军先败后胜,但也伤亡惨重,无力再攻汴州。
天佑十八年(921年)赵国发生内乱,赵王王镕为其养子张文礼所杀,李存勖派大军讨伐,张文礼病死。 天佑十九年(922年)李存审攻陷镇州,杀张文礼之子张处瑾,自此赵地彻底为前晋所有。
天佑二十年(923年)四月,李存勖在魏州称帝,改元同光,沿用"唐"为国号,又追赠父祖三代为皇帝,与唐高祖、唐太宗、唐懿宗、唐昭宗并列为七庙,以表示自己是唐朝的合法继承人,史家称之为后唐。
同光元年(923年)十月初二,李存勖亲率大军由杨刘渡河,初三,进至郓州,以部将李嗣源为前锋。当夜越过汶水,次日晨与梁将王彦章相遇,一战而胜,并克中都(今山东汶上),擒王彦章。他又采纳李嗣源关于兵贵神速、急趋汴州的建议,命其率前军当夜出发,自率主力继后。初七,进至曹州(今山东曹县西北),梁将不战而降,朱友贞见援兵无望而自杀。初九,唐军至汴州,王瓒开门出降。十二日,段凝率军五万到封丘(今属河南)请降,后梁灭亡。
李存勖入汴州后,贬郑珏为莱州司户参军,萧顷登州司户参军;杀李振、赵岩、张汉杰、朱珪,灭其族。
李存勖与伶人同台演出,并起艺名"李天下";因喜好演戏,而对伶人特别宠信,以致出现了伶人干政的古代少有的现象。唐末宦官大批被杀,侥幸逃生的宦官多藏匿民间。李存勖登基后,宦官势力死灰复燃。李存勖身边的宦官多达近千人。且以宦官为监军,牵制军中将领。李存勖听信伶人和宦官的谗言,疏忌宿将,弄得人人自危。大将李嗣源可谓忠心耿耿,也遭到猜忌。
租庸使孔谦横征暴敛,百姓怨声载道,李存勖反而认为孔谦理财有功,赐"丰财赡国功臣"称号。 李存勖听信宦官之言,设立内府和外府;导致外府常虚竭无馀而内府山积。 当时政制混乱,政出多门。皇太后诰命,皇后教令,与庄宗的制敕交行于地方,地方官府都照办不误。
同光二年(925年)南汉国主刘龑听说李存勖灭梁,心生恐惧,派使者进贡,并窥探虚实。使者何词返汉后,向刘龑汇报说:李存勖"骄淫无政,不足畏也"。
同光三年(926年)九月,庄宗命魏王李继岌,枢密使郭崇韬,领兵六万,自凤翔走大散关入蜀;另以高季兴为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,率荆南军攻取夔州、忠州、万州等地。
同光三年(926年)十月,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绍深攻克威武城;蜀将王承捷以凤、兴、文、扶四州降唐。唐军长驱直入,李继岌兵临兴州,蜀将宋光葆以梓、绵、剑、龙、普五州降唐;而后蜀国武定节度使王承肇、山南节度使王宗威、阶州刺史王承岳分别献城投降;只有蜀国天雄节度使王承休与副使安重霸打算出秦州攻打唐军,至茂州,兵马仅剩两千,安重霸见大势已去,以秦、陇二州降唐。高季兴乘势率水军逆流而上,攻打施州。蜀国峡路招讨使张武用铁锁断绝长江航路,大败荆南军,高季兴乘轻舟逃走。不久,张武闻北路失败,便以夔、忠、万三州降唐。十一月,唐军昼夜兼行,至利州,王宗弼闻风弃城西逃。李继岌率大军向剑州、绵州、汉州推进。蜀国武信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寿以遂、合、渝、泸、昌五州降唐。李绍琛到达绵州时,绵江浮桥已被蜀兵破坏。为速取蜀国,李绍琛乘蜀兵溃败之机,率大军骑马渡江,入鹿头关,攻克汉州,直逼成都。
同光三年(926年)十一月二十六日,李继岌率大军到达成都,翌日,蜀主王衍出降,前蜀灭亡。
清泰二年(935年)末帝派遣武宁节度使张敬达领兵驻屯在代州,牵制并监视石敬瑭。 清泰三年(936年)末帝又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,企图以此消弱石敬瑭兵权。石敬瑭拒绝调任。于是,石敬瑭叛变,同时石敬瑭还上表指责李从珂即位非法,应立即将皇位让给许王。末帝大怒,撕毁奏表,削其官爵。
清泰三年(936年)五月,末帝任命建雄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,杨光远为副使,率大军讨伐石敬瑭。 唐军包围了太原,筑长围以围困晋阳。石敬瑭遣使向契丹求救,表示愿意割地称臣。九月,契丹主耶律德光亲率五万兵马增援石敬瑭,唐军与辽晋联军大战于团柏谷,唐军大败,死伤万余人。随后,石敬瑭与契丹军得以顺利南下进逼京师洛阳。途中先锋指挥使安审信、振武守将安重荣、彰圣指挥使张万迪等将纷纷归降石敬瑭,后唐统治岌岌可危,处于即将全面崩溃的前夕。
清泰三年(936年)十一月二十六日,末帝见大势已去,带传国玉玺与曹太后、刘皇后以及太子李重美等人登上玄武楼,自焚而死,后唐遂亡。
沙陀的族源
《册府元龟》(以下简称《元龟》)卷九五六《外臣部·种族》云:
沙陀突厥,本西突厥之别种也。
《新唐书》(以下简称《新书》)卷二一八《沙陀传》云:
沙陀,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。
《新五代史》(以下简称《新史》)卷四《唐庄宗纪》云:
其先本号朱邪,盖出于西突厥。
上述诸书,都指出沙陀出于西突厥,尤其是《新书》,明确指出其出自“西突厥别部处月种”。韩国磐先生则认为:“沙陀源出于突厥别部,或即同罗、仆固之后。” [1]陶懋炳先生说得很肯定:“沙陀族源出于突厥别部,属同罗、仆骨部。突厥为唐击破,又转属薛延陀。七世纪中,唐太宗灭薛延陀,‘分同罗、仆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。’因当地有沙碛,故称沙陀。” [2] 徐庭云先生则进一步发挥,认为史籍中记载的“沙陀的重要族源是西突厥,这无疑是正确的;与此同时,这些记载显然将沙陀复杂的族源问题简单化了,即以沙陀与西突厥的关系而论,也不是一句简单的‘西突厥别部处月种’所能概括的。‘沙陀’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,根据现有的资料,其族源起码还应包括突厥、回纥、粟特3个主要的民族成分, 每一民族之中,又包括若干部落。”
并且说:“自然,这些远远不足以概括沙陀人的族属, 例如:沙陀人中还可能有鞑靼的成分,以至到了元代,一些汪古人自称是沙陀人的后裔。” [3] 这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,究竟应该如何认识沙陀的族源。笔者认为,要解决这一问题,首先应该明确“族源”一词的概念。
对于 “族源”一词如何解释?笔者查阅了许多工具书,没能找到现成的答案,或许是因为这一词汇过于普通或明了的缘故吧,这些工具书都不予收录。不过,对于“源” 字,诸书倒均有解释。以颇具权威的《辞源》的解释为例:“源,水流起头的地方。” [4]《汉语大字典》除上述解释外,又补上一条:“来源、根源。” [5] 据此,笔者以为,“族源”, 也就是一个民族起头的那个氏族或部落。沙陀的族源,也就是沙陀族起头的氏族和部落。如果这样理解不错的话,那么,第一,粟特人不是沙陀的族源。
徐文认为:“早在沙陀人进入中原地区之前, 突厥地区的粟特人便与突厥人融合,开始了所谓粟特人突厥化的过程。作为西突厥别部的沙陀人中自然也不例外地融入了粟特人的成份”。按这只是一种推测。欧阳修说:“当是时, 西突厥有铁勒、延陀、阿史那之类为最大;其别部有同罗、仆骨、拔野古等以十数,盖其小者也;又有处月、处密诸部,又其小者也。”[6] 所以,粟特人即使是在突厥化,恐怕也未必就会融合到沙陀人中间。至若以“沙陀三部落”的称呼作为粟特人是沙陀族源最重要的证据,则更加难以成立。
从人们将沙陀人与粟特人合称为“沙陀三部落”,可见其关系至为密切,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融为一体。如安叔千,“沙陀三部落种也”[7];安仁义,“沙陀人”[8];康义诚,“代北三部落人也”[9]; 米志诚,“沙陀部人”[10];等等。安叔千、安仁义、康义诚、米志诚,从其姓氏看,显然为昭武九姓胡人即粟特人,而史籍却将他们写作“沙陀三部落人”、“代北三部落人”、“沙陀部人”、“沙陀人”,可见代北地区的沙陀人与粟特人已融为一体。但是,据笔者所见到的材料,“沙陀三部落”称呼的出现,最早在文宗开成年间(836—840),《旧唐书》(以下简称《旧书》)卷一六一《刘沔传》云:
开成中,党项杂虏大扰河西,沔率吐浑、契苾、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、马三千骑,径至银、夏讨袭。
而“沙陀”以部族名出现,最晚在玄宗时就见诸记载,《全唐文》卷二八四张九龄《敕伊吾军使张楚宾书》云:
近得卿表,知沙陀入界,此为刘涣凶逆,处置狂疏,遂令此蕃,暂有迁转。今刘涣伏法,远近知之,计沙陀部落,当自归本处。
刘涣“凶逆”“伏法”一事,在开元二十二年(734),下至文宗开成年间,至少已有102年,即在“沙陀三部落”称呼出现的一个多世纪以前, 沙陀部族已经形成。因此,可以说沙陀部族中融入了粟特人的成分,但却不能以此证明粟特人是沙陀的族源,至于汪古人自称为沙陀人的后裔,也只能说是一些达靼人或回鹘人加入了沙陀民族共同体 [11],同样不能说明他们是沙陀人的族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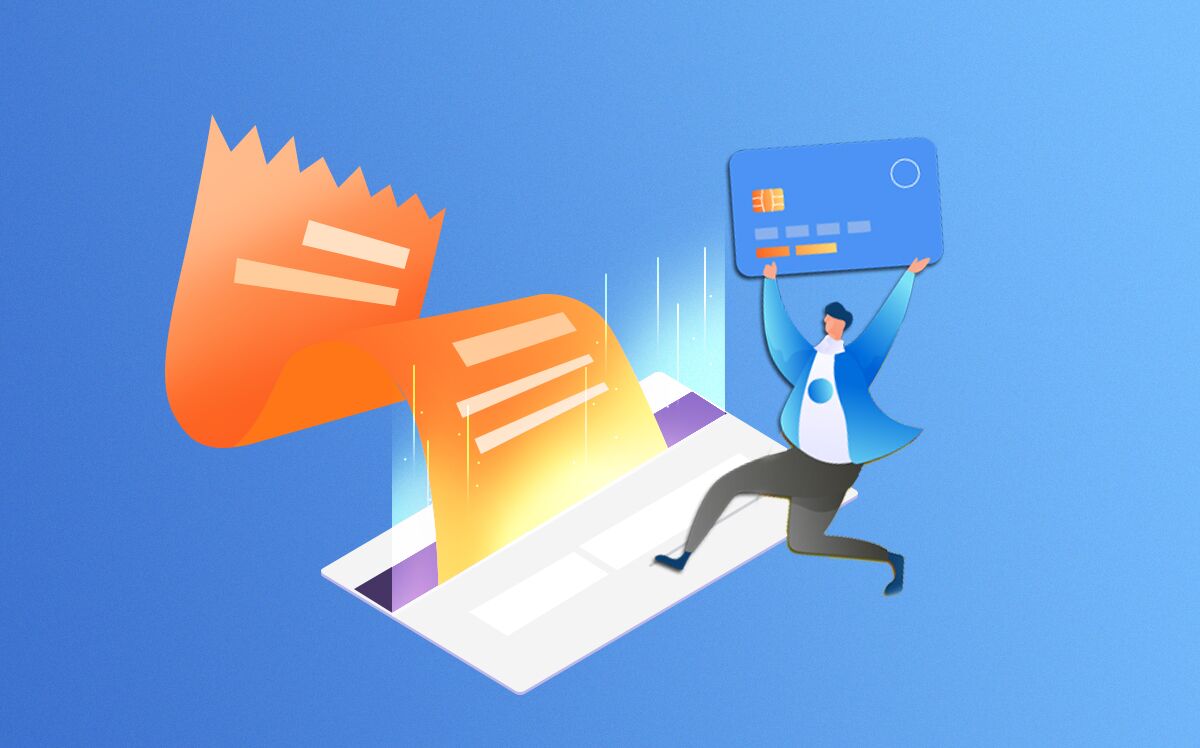






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
营业执照公示信息